排污獲刑:環境保護的司法進步
來源: 點擊量:5270
(本文來源:中國泵閥商務網www.ichsh.com,如需轉載請與本網聯系。)
BF35導讀:兩高司法解釋具體羅列了14項“嚴重污染環境”的標準,為辦案提供了具體的操作細則。污染環境罪從結果犯轉變為行為犯,便于更嚴厲打擊環境犯罪,從源頭控制環境犯罪。去年,浙江全省法院共審結22起污染環境罪案件,判處35人。
1月14日,記者獲悉,未經環評許可卻從事酸洗項目,并將有害廢水直接排入江中,浙江臺州市黃巖區恒光金屬加工有限公司及股東周正友近日因犯污染環境罪被臺州黃巖區人民法院依法判處罰金10萬元和有期徒刑1年3個月。
前不久,即1月6日,法治周末記者還從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法院辦公室了解到,企業主鄧善飛因排放重金屬超標的污水,犯污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
去年12月30日,浙江省人民法院通報,過去一年全省法院共審結22起污染環境罪案件,判處35人,刑期高的達3年6個月;依法裁定2287件環境污染行政處罰案件準予執行。
在以往,企業主很難因污染環境獲刑。去年6月18日,高人民法院和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司法解釋”),其中界定了嚴重污染環境的14項標準。自此,如何用刑事手段懲治環境污染者,有了具體的操作細則。
非法排污獲刑
位于永康市方巖鎮兩頭門村內,一間80平方米左右的“小黑屋”,陰暗潮濕的土地上擺放了大大小小的水桶,桶里盛放著泛著綠瑩瑩色澤的污水。
這是一家電鍍廠,負責人叫胡勇健。
在浙江金華的永康、東陽等地,這類電鍍廠比比皆是。記者了解到,永康被稱為“五金之都”,在這座五金業發達的城市,電鍍廠作為五金產業鏈不可或缺的環節應運而生。
電鍍,是利用電解方法使金屬或合金沉積在工件表面,以形成均勻、致密、結合力良好的金屬層。電鍍加工過程中,會產生含有大量重金屬的污染物,這類污染物的排放有著嚴格的標準。早在2008年,我國就發布了GB21900-2008《電鍍污染物排放標準》。
據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出于經濟效益考慮,永康當地不乏企業主未經審批開辦電鍍廠。胡勇健的電鍍廠正是其中之一。他開辦電鍍廠私自排放污水有著僥幸心理——按照以往的經驗,萬一被環保部門查處多就是罰款或關停。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換個地方重新再開,違法成本極低。
去年11月8日,電鍍廠排放的綠色污水引起了當地村民的注意,馬上有人向環保部門舉報。接到舉報材料后,永康市環保局的工作人員趕往現場取證并向公安機關移交了案件。
據了解,去年6月18日新出臺的兩高司法解釋規定,“非法排放含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嚴重危害環境,損害人體健康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法律授權指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三倍以上”,屬嚴重污染環境。
永康市環境保護監測站對取得的水樣進行了檢測,得出如下結論:該電解加工產生的廢水水樣中總鉻、總鎳、總銅、PH值濃度均不符合GB21900-2008《電鍍污染物排放標準》表2中標準限值。其中,總鉻指標超過250倍以上,總鎳指標超過50倍以上,總銅指標超過60倍以上,屬嚴重污染環境。
此后,浙江省環境保護廳出具了關于檢測報告的認可意見。
永康市公安機關查明,去年10月份以來,胡勇健在當地經營電鍍廠,在未采取有效措施的情況下,將廠里加工所產生的廢水直接排放于周圍環境。
去年12月13日,永康市法院審理認為,胡勇健違反國家規定,排放有毒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其行為已構成污染環境罪,對胡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
這并不是浙江省查處的起“排污入刑案”。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去年7月,金華浦江縣檢察院以污染環境罪批捕了一家磨盤加工廠的企業主鄧善飛。
據了解,浦江縣是“水晶之鄉”,在水晶生產過程中,磨盤是必備工具。鄧善飛所開的加工廠,主要是給水晶磨盤上砂,在此過程中,會使用到重金屬鎳以及一些強酸。為了偷排廢水,鄧善飛在加工點墻角挖了一個洞,將廢水直接排放到門口的小水溝,終流入江中。當地環保部門在查處鄧善飛的加工廠后,檢測得出3個點的廢水樣本分別超過國家標準1萬多倍、47倍和1000多倍。
去年11月19日,鄧善飛因犯污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3000元,成為浙江首例“排污入刑案”。
從結果犯到行為犯
前不久,浙江高院通報,過去一年全省法院共審結22起污染環境罪案件,判處35人;依法裁定2287件環境污染行政處罰案件準予執行。
針對審處此類案件,浙江高院提出兩點舉措:降低環境污染的構罪標準,實施“舉證責任倒置”。一方面,由原本的偏重結果到偏重行為,以往要有重大人員傷亡或者經濟損失才能追究法律責任,現在只要存在污染行為,就可以處罰。另一方面,環境污染案中將由污染方來承擔舉證責任,如果不能提供相應證明,原告方意見即或成立。
參與辦案的永康市公安局治安大隊行動中隊中隊長俞竣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過去企業主僥幸心理嚴重、法律意識不強,以為排放廢水就跟往河里扔垃圾一樣普通,僅僅是罰款或關停就可以了事。“兩高司法解釋的出臺,是國家對于環境保護方面的司法進步。”
俞竣向記者透露,早在2012年,當地公安機關就在環保部門設立了專門的聯絡室,2013年改為警務室,專門處理環保部門移交過來的污染環境案。但是,在取證這一環節,存在諸多困難。
首當其沖的是取樣難。“對于水污染、放射性污染、具備傳染性的有毒有害物質等,取樣上存在一定困難。”其次,是鑒定難。據俞竣介紹,我國具備環境司法鑒定資質的機構并不多,僅有三家。
記者查詢獲悉,三家機構分別是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司法鑒定所、福建力普環境司法鑒定所、連云港市環境司法鑒定所。其中,福建力普環境司法鑒定所是我國陸源污染的主要環境污染司法鑒定機構,曾參加過紫金礦業、福建泉港污水處理廠等污染大案的環境司法鑒定。
除了取樣、鑒定環節存在一定困難,俞竣表示,過去我國法律對污染環境罪強調的是結果犯,即行為人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加以認定,如該行為造成嚴重后果,則以污染環境罪論處。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為了防治污染、保護環境,國家先后制定了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法律,以及《放射防護條例》、《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農藥安全使用條例》等一系列專門法規。
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俞竣表示,這里面對于何為“嚴重污染環境”的內容規定的并不是很詳細,實際環節很難操作。在以往,大部分案件只能依據治安處罰法進行治安處罰,對不法企業主的震懾力不大。
“不過,”俞竣話鋒一轉,在兩高司法解釋中具體羅列了14項“嚴重污染環境”的標準,為辦案提供了具體的操作細則,“辦案一下子找到了方向。污染環境罪從結果犯轉變為行為犯,便于更嚴厲打擊環境犯罪、從源頭控制環境犯罪。”
采訪中,記者獲悉,兩高司法解釋的另一亮點就是在第十一條規定了“縣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出具的監測數據,經省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認可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一規定,大大解決了以往取證難、鑒定難的問題。
俞竣表示,在胡勇健案中,永康市環境保護監測站的檢測報告經省環保廳認可,就直接作為證據使用了。
試水環境公益訴訟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早在兩高司法解釋出臺之前,浙江環保部門一直在積極探索污染環境案中的環境公益訴訟,力求形成更加嚴厲的環保執法態勢,查處各類違法排污行為。
2010年8月,浙江省檢察院和省環保廳聯合出臺了《關于積極運用民事行政檢察職能加強環境保護的意見》,其中提到對環境公益訴訟的探索:“各地檢察機關和環保部門要積極探索環境公益訴訟,有條件的縣(市、區)可以與當地人民法院協調先行試點。對環保部門作為原告代表公共利益提起環境污染民事公益訴訟的,檢察機關應當予以支持,為今后我省環境公益訴訟的健康開展積累經驗。”
此后,嘉興市檢察院和環保局聯合制定《關于環境保護公益訴訟的若干意見》,正式啟動嘉興市環境保護公益訴訟制度,這在浙江開了先河。
2011年11月,浙江平湖市法院受理首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案。該案中,檢察機關以公益訴訟原告身份,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嘉興市綠誼環保服務有限公司等五被告,賠償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54.1萬元。
2011年12月16日,歷經40天審理后,平湖市檢察院與嘉興綠誼環保服務有限公司等五公司之間達成和解協議:嘉興綠誼環保服務有限公司支付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541373元,并承擔案件訴訟費4607元。
盡管平湖檢察機關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受到質疑,但在平湖案審結后,2012年7月,嘉興市桐鄉法院再次受理了由桐鄉市檢察院提起的訴張某賠償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兩萬元的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案,這是浙江首例針對自然人提起的環境保護公益訴訟。
桐鄉市檢察機關認為,被告張某明知自己在經營活動中產生的危險物質可能對環境有重大污染,既未向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申報登記,也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嚴重損害了環境公共利益,故提起公益訴訟。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2010年5月至2012年8月期間,嘉興市共向檢察機關移送環保違法案件55起,其中檢察院發立案決定書33份,發檢察建議書48份,對兩個拒不執行停止生產處罰決定書的當事人實行司法拘留,對環境違法者起到極大的震懾作用。
有評論人士指出,公益訴訟模式的引入對于探索突破現有“環保困局”意義重大。檢察機關充當原告不僅有助于發揮檢察機關的專業性和程序性優勢,而且避免了民眾直接面對污染企業時可能碰到的“不對等”情形——其中涉及經濟實力、資源占有等多方面的“不對等”。
記者調查獲悉,早在2010年12月,嘉興市環保聯合會宣告成立,這是一個從事環境公益事業、非營利性的環保民間社團組織,由嘉興市環境科學學會、嘉興市節能協會和嘉興市環保產業協會等五家社團發起。為了明確環境公益訴訟主體,去年上半年,嘉興市環保局會同嘉興市檢察院和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商榷,后報請浙江省人民法院審核,請示確定嘉興市環保聯合會作為環保公益訴訟案件的起訴主體。
1月7日,法治周末記者從嘉興市環保局了解到,浙江省高院已經批準了嘉興市環保聯合會的公益訴訟主體資格。
記者看到,浙江省高院浙高法【2013】136號文件批復“《民事訴訟法》……對有權提起公益訴訟的機關和有關組織沒有明確規定,根據當地實際,在一個地區確定一家有關組織作為環境污染公益訴訟主體符合立法精神,可先行探索,故原則同意嘉興市環境保護局推薦的嘉興市環保聯合會可作為當地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案件的起訴主體”。
文件還指出,審查受理公益訴訟案件應從嚴審慎把握,特別要注意是否符合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一基本特點。對受害人可以確定的案件不能作為公益訴訟處理。另外,應建立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案件賠償金的使用、監管等制度,堅決防止賠償金的不當使用。
記者了解到,現行環境保護法自1989年正式頒行以來,至今沒有實質修改,而這期間正是我國環境急速惡化的30年,不少環保專家和學者呼吁放開公益訴訟主體資格限制,建立環境信息統一公開平臺,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加強行政部門履職監督。
BF35導讀:兩高司法解釋具體羅列了14項“嚴重污染環境”的標準,為辦案提供了具體的操作細則。污染環境罪從結果犯轉變為行為犯,便于更嚴厲打擊環境犯罪,從源頭控制環境犯罪。去年,浙江全省法院共審結22起污染環境罪案件,判處35人。
1月14日,記者獲悉,未經環評許可卻從事酸洗項目,并將有害廢水直接排入江中,浙江臺州市黃巖區恒光金屬加工有限公司及股東周正友近日因犯污染環境罪被臺州黃巖區人民法院依法判處罰金10萬元和有期徒刑1年3個月。
前不久,即1月6日,法治周末記者還從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法院辦公室了解到,企業主鄧善飛因排放重金屬超標的污水,犯污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
去年12月30日,浙江省人民法院通報,過去一年全省法院共審結22起污染環境罪案件,判處35人,刑期高的達3年6個月;依法裁定2287件環境污染行政處罰案件準予執行。
在以往,企業主很難因污染環境獲刑。去年6月18日,高人民法院和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司法解釋”),其中界定了嚴重污染環境的14項標準。自此,如何用刑事手段懲治環境污染者,有了具體的操作細則。
非法排污獲刑
位于永康市方巖鎮兩頭門村內,一間80平方米左右的“小黑屋”,陰暗潮濕的土地上擺放了大大小小的水桶,桶里盛放著泛著綠瑩瑩色澤的污水。
這是一家電鍍廠,負責人叫胡勇健。
在浙江金華的永康、東陽等地,這類電鍍廠比比皆是。記者了解到,永康被稱為“五金之都”,在這座五金業發達的城市,電鍍廠作為五金產業鏈不可或缺的環節應運而生。
電鍍,是利用電解方法使金屬或合金沉積在工件表面,以形成均勻、致密、結合力良好的金屬層。電鍍加工過程中,會產生含有大量重金屬的污染物,這類污染物的排放有著嚴格的標準。早在2008年,我國就發布了GB21900-2008《電鍍污染物排放標準》。
據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出于經濟效益考慮,永康當地不乏企業主未經審批開辦電鍍廠。胡勇健的電鍍廠正是其中之一。他開辦電鍍廠私自排放污水有著僥幸心理——按照以往的經驗,萬一被環保部門查處多就是罰款或關停。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換個地方重新再開,違法成本極低。
去年11月8日,電鍍廠排放的綠色污水引起了當地村民的注意,馬上有人向環保部門舉報。接到舉報材料后,永康市環保局的工作人員趕往現場取證并向公安機關移交了案件。
據了解,去年6月18日新出臺的兩高司法解釋規定,“非法排放含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嚴重危害環境,損害人體健康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法律授權指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三倍以上”,屬嚴重污染環境。
永康市環境保護監測站對取得的水樣進行了檢測,得出如下結論:該電解加工產生的廢水水樣中總鉻、總鎳、總銅、PH值濃度均不符合GB21900-2008《電鍍污染物排放標準》表2中標準限值。其中,總鉻指標超過250倍以上,總鎳指標超過50倍以上,總銅指標超過60倍以上,屬嚴重污染環境。
此后,浙江省環境保護廳出具了關于檢測報告的認可意見。
永康市公安機關查明,去年10月份以來,胡勇健在當地經營電鍍廠,在未采取有效措施的情況下,將廠里加工所產生的廢水直接排放于周圍環境。
去年12月13日,永康市法院審理認為,胡勇健違反國家規定,排放有毒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其行為已構成污染環境罪,對胡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
這并不是浙江省查處的起“排污入刑案”。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去年7月,金華浦江縣檢察院以污染環境罪批捕了一家磨盤加工廠的企業主鄧善飛。
據了解,浦江縣是“水晶之鄉”,在水晶生產過程中,磨盤是必備工具。鄧善飛所開的加工廠,主要是給水晶磨盤上砂,在此過程中,會使用到重金屬鎳以及一些強酸。為了偷排廢水,鄧善飛在加工點墻角挖了一個洞,將廢水直接排放到門口的小水溝,終流入江中。當地環保部門在查處鄧善飛的加工廠后,檢測得出3個點的廢水樣本分別超過國家標準1萬多倍、47倍和1000多倍。
去年11月19日,鄧善飛因犯污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3000元,成為浙江首例“排污入刑案”。
從結果犯到行為犯
前不久,浙江高院通報,過去一年全省法院共審結22起污染環境罪案件,判處35人;依法裁定2287件環境污染行政處罰案件準予執行。
針對審處此類案件,浙江高院提出兩點舉措:降低環境污染的構罪標準,實施“舉證責任倒置”。一方面,由原本的偏重結果到偏重行為,以往要有重大人員傷亡或者經濟損失才能追究法律責任,現在只要存在污染行為,就可以處罰。另一方面,環境污染案中將由污染方來承擔舉證責任,如果不能提供相應證明,原告方意見即或成立。
參與辦案的永康市公安局治安大隊行動中隊中隊長俞竣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過去企業主僥幸心理嚴重、法律意識不強,以為排放廢水就跟往河里扔垃圾一樣普通,僅僅是罰款或關停就可以了事。“兩高司法解釋的出臺,是國家對于環境保護方面的司法進步。”
俞竣向記者透露,早在2012年,當地公安機關就在環保部門設立了專門的聯絡室,2013年改為警務室,專門處理環保部門移交過來的污染環境案。但是,在取證這一環節,存在諸多困難。
首當其沖的是取樣難。“對于水污染、放射性污染、具備傳染性的有毒有害物質等,取樣上存在一定困難。”其次,是鑒定難。據俞竣介紹,我國具備環境司法鑒定資質的機構并不多,僅有三家。
記者查詢獲悉,三家機構分別是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司法鑒定所、福建力普環境司法鑒定所、連云港市環境司法鑒定所。其中,福建力普環境司法鑒定所是我國陸源污染的主要環境污染司法鑒定機構,曾參加過紫金礦業、福建泉港污水處理廠等污染大案的環境司法鑒定。
除了取樣、鑒定環節存在一定困難,俞竣表示,過去我國法律對污染環境罪強調的是結果犯,即行為人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加以認定,如該行為造成嚴重后果,則以污染環境罪論處。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為了防治污染、保護環境,國家先后制定了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法律,以及《放射防護條例》、《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農藥安全使用條例》等一系列專門法規。
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俞竣表示,這里面對于何為“嚴重污染環境”的內容規定的并不是很詳細,實際環節很難操作。在以往,大部分案件只能依據治安處罰法進行治安處罰,對不法企業主的震懾力不大。
“不過,”俞竣話鋒一轉,在兩高司法解釋中具體羅列了14項“嚴重污染環境”的標準,為辦案提供了具體的操作細則,“辦案一下子找到了方向。污染環境罪從結果犯轉變為行為犯,便于更嚴厲打擊環境犯罪、從源頭控制環境犯罪。”
采訪中,記者獲悉,兩高司法解釋的另一亮點就是在第十一條規定了“縣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出具的監測數據,經省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認可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一規定,大大解決了以往取證難、鑒定難的問題。
俞竣表示,在胡勇健案中,永康市環境保護監測站的檢測報告經省環保廳認可,就直接作為證據使用了。
試水環境公益訴訟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早在兩高司法解釋出臺之前,浙江環保部門一直在積極探索污染環境案中的環境公益訴訟,力求形成更加嚴厲的環保執法態勢,查處各類違法排污行為。
2010年8月,浙江省檢察院和省環保廳聯合出臺了《關于積極運用民事行政檢察職能加強環境保護的意見》,其中提到對環境公益訴訟的探索:“各地檢察機關和環保部門要積極探索環境公益訴訟,有條件的縣(市、區)可以與當地人民法院協調先行試點。對環保部門作為原告代表公共利益提起環境污染民事公益訴訟的,檢察機關應當予以支持,為今后我省環境公益訴訟的健康開展積累經驗。”
此后,嘉興市檢察院和環保局聯合制定《關于環境保護公益訴訟的若干意見》,正式啟動嘉興市環境保護公益訴訟制度,這在浙江開了先河。
2011年11月,浙江平湖市法院受理首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案。該案中,檢察機關以公益訴訟原告身份,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嘉興市綠誼環保服務有限公司等五被告,賠償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54.1萬元。
2011年12月16日,歷經40天審理后,平湖市檢察院與嘉興綠誼環保服務有限公司等五公司之間達成和解協議:嘉興綠誼環保服務有限公司支付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541373元,并承擔案件訴訟費4607元。
盡管平湖檢察機關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受到質疑,但在平湖案審結后,2012年7月,嘉興市桐鄉法院再次受理了由桐鄉市檢察院提起的訴張某賠償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兩萬元的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案,這是浙江首例針對自然人提起的環境保護公益訴訟。
桐鄉市檢察機關認為,被告張某明知自己在經營活動中產生的危險物質可能對環境有重大污染,既未向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申報登記,也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嚴重損害了環境公共利益,故提起公益訴訟。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2010年5月至2012年8月期間,嘉興市共向檢察機關移送環保違法案件55起,其中檢察院發立案決定書33份,發檢察建議書48份,對兩個拒不執行停止生產處罰決定書的當事人實行司法拘留,對環境違法者起到極大的震懾作用。
有評論人士指出,公益訴訟模式的引入對于探索突破現有“環保困局”意義重大。檢察機關充當原告不僅有助于發揮檢察機關的專業性和程序性優勢,而且避免了民眾直接面對污染企業時可能碰到的“不對等”情形——其中涉及經濟實力、資源占有等多方面的“不對等”。
記者調查獲悉,早在2010年12月,嘉興市環保聯合會宣告成立,這是一個從事環境公益事業、非營利性的環保民間社團組織,由嘉興市環境科學學會、嘉興市節能協會和嘉興市環保產業協會等五家社團發起。為了明確環境公益訴訟主體,去年上半年,嘉興市環保局會同嘉興市檢察院和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商榷,后報請浙江省人民法院審核,請示確定嘉興市環保聯合會作為環保公益訴訟案件的起訴主體。
1月7日,法治周末記者從嘉興市環保局了解到,浙江省高院已經批準了嘉興市環保聯合會的公益訴訟主體資格。
記者看到,浙江省高院浙高法【2013】136號文件批復“《民事訴訟法》……對有權提起公益訴訟的機關和有關組織沒有明確規定,根據當地實際,在一個地區確定一家有關組織作為環境污染公益訴訟主體符合立法精神,可先行探索,故原則同意嘉興市環境保護局推薦的嘉興市環保聯合會可作為當地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案件的起訴主體”。
文件還指出,審查受理公益訴訟案件應從嚴審慎把握,特別要注意是否符合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一基本特點。對受害人可以確定的案件不能作為公益訴訟處理。另外,應建立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案件賠償金的使用、監管等制度,堅決防止賠償金的不當使用。
記者了解到,現行環境保護法自1989年正式頒行以來,至今沒有實質修改,而這期間正是我國環境急速惡化的30年,不少環保專家和學者呼吁放開公益訴訟主體資格限制,建立環境信息統一公開平臺,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加強行政部門履職監督。
- 版權與免責聲明:凡本網注明“來源:泵閥商務網”的所有作品,均為浙江興旺寶明通網絡有限公司-泵閥商務網合法擁有版權或有權使用的作品,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泵閥商務網www.ichsh.com”。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 本網轉載并注明自其它來源(非泵閥商務網)的作品,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或和對其真實性負責,不承擔此類作品侵權行為的直接責任及連帶責任。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從本網轉載時,必須保留本網注明的作品第一來源,并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周內與本網聯系,否則視為放棄相關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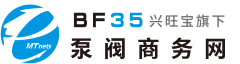







評論